郭文安,湖南炎陵人,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组组长,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长期担任《教育研究与实验》副主编、主编;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研究会会员,湖北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教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道俊教授与他共同倡导的“主体性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教育思潮和学术流派。
一本教科书 一生教育情
初见郭文安教授,只觉得眼前这位老人并不像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者。回首过往,他用温和的语调,娓娓道来。
1952年,郭文安成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第一届学生,与华师结缘。从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岁华诞,屈指算来,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六十九年。六十九年间,他甘为人师,辛勤培育学生;他脚踏实地,认真做好科研,他笔耕不辍,一生精心编撰《教育学》教材。

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由王道俊先生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持续畅销近40年、共编印了7版、累计发行近800万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堪称经典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也许很少人知道,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郭文安就开始参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作。
1956年,郭文安毕业留校,成为教育系的一名老师,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尤其是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要性不言而喻。五十年代末,在时任学校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教育系成立了《教育学》教材编写组,开始推进编写工作。编写组克服了诸多困难,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最终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于1962年出版了《教育学》教材。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
“据说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师范院校同时编写《教育学》教材,号称‘五朵金花’。不过,这‘五朵金花’只开了两朵。一朵我们学校的,一朵是华东师大主编的。”郭文安回忆道:“如今看来,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并锻炼了编写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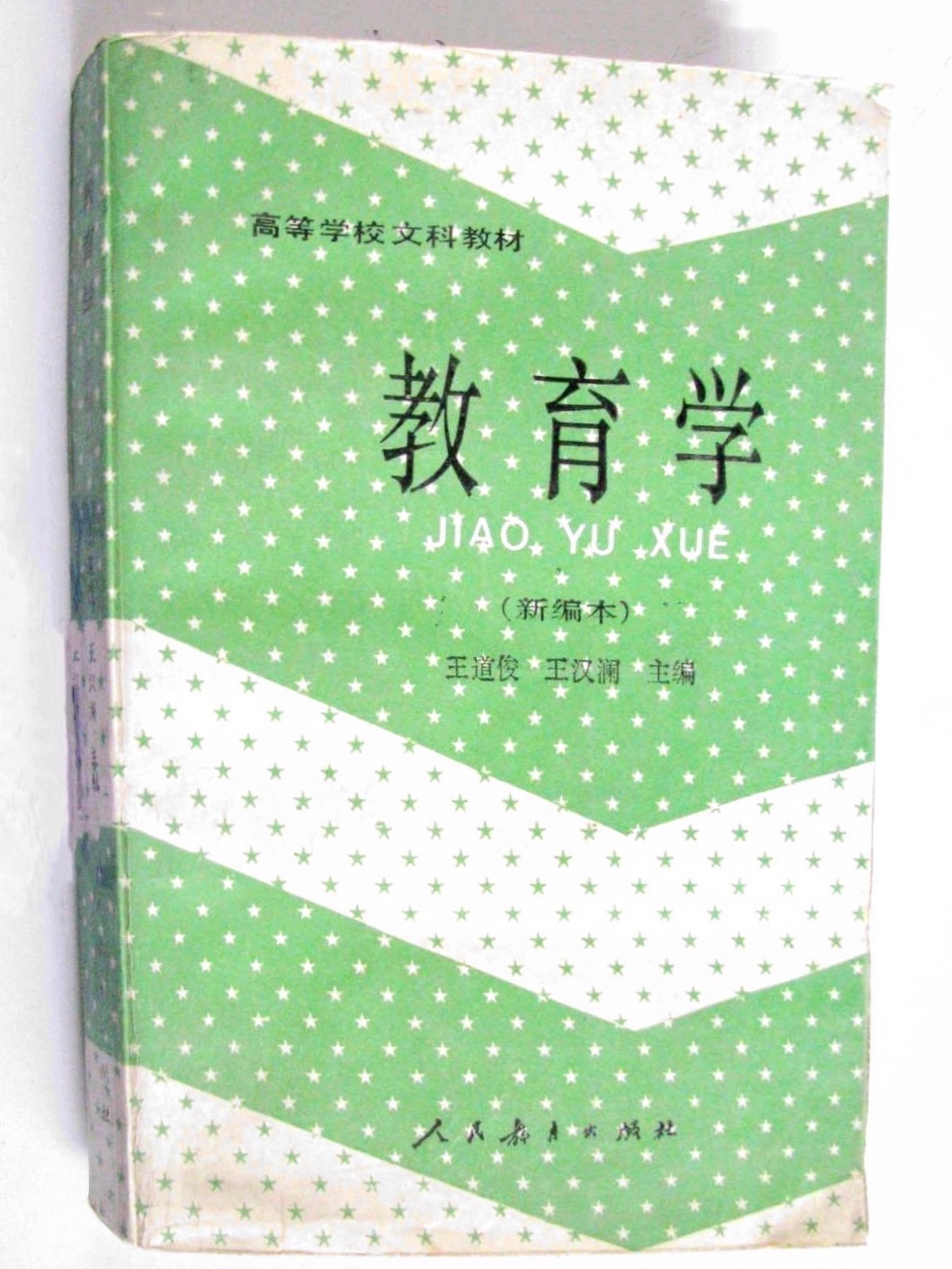
教育学(新编本)
1978年,郭文安与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参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材,俗称五院校《教育学》。“我开始的分工是撰写‘德育’这一章。后来,王道俊老师还专门叫我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
1980年,五院校《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反响良好,几经修改,数次再版。彼时,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建设,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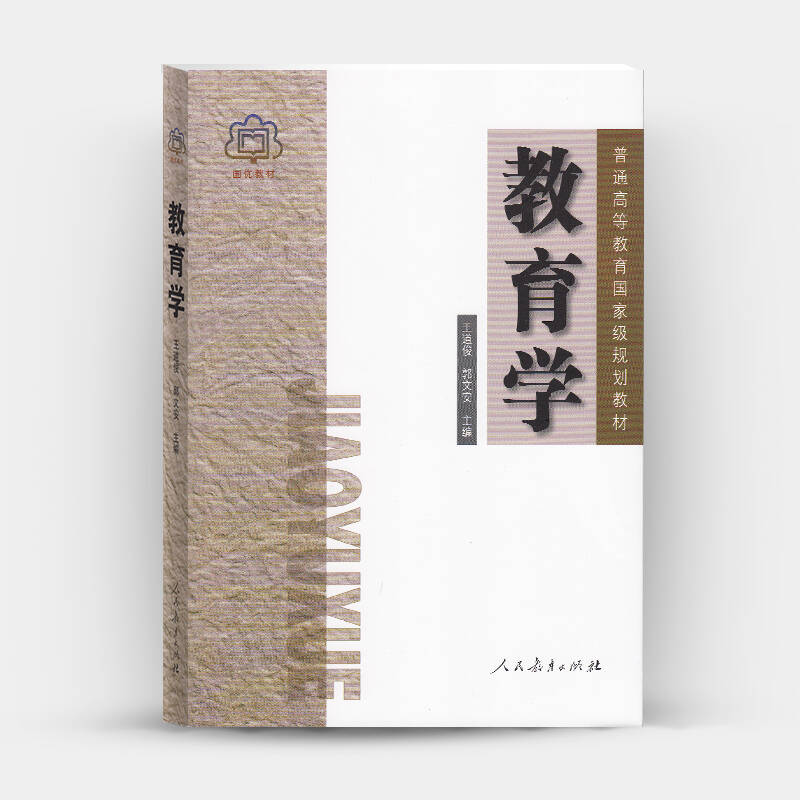
教育学(第六版)
郭文安记得,在五院校《教育学》出版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学校又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的新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力争在教材质量上有显著提高。
谈起这次编写,即便时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数家珍。“刚开始要求我写德育(上、下)与班主任,共三章,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任务。稿子交上去后,据王(道俊)老师说,领导们看了还比较肯定,后来又把教学(上、中、下)三章交给我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我也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书来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看了之后,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更新之外,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算是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郭文安笑言,“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例,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写作进度有点儿慢。王道俊老师看我拖了两年迟迟没有交稿,放心不下,还专门跑到我家里,问我写得如何。我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王老师看了之后,就说你不要赶时间,继续安心写吧。王老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不光是我,其实王老师承担的‘教育目的’一章,写得比我还认真。书稿交上去以后,很快就通过了,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
1989年,《教育学》出版,因为编写方式与内容较之以往有较大的改进,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编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教育学(第七版)
从1989年的新编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数十年间,郭文安一直把这本教材的修订放在心上,他与王道俊老师团队一起,不断在修订中更新学科进展,力求反映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征与新需求。其间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
与学者个人著书立说相比,或许编写教材并不能算作“重量级”成果。对此,郭文安并不是不知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常常有人议论,花那么多精力去编教材,还不如多搞一些科研,写点文章、专著实在些……教材的编写要依据学科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特点和水平,其选编的内容有比较基础、成熟、精要、容易取得共识等不成文的严格要求,在编写格式上又讲究严格的规范,作为高校教材还必须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学科发展前沿与时代精神,这样就使教材编写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与难度。说实话,要东拼西凑编一本讲义性教材也许比较容易,但要编撰出一本反映学科发展精粹和前沿,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自己特色的《教育学》教材实在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艰难困苦之事。”
即便觉得“极其折磨人”,郭文安依然愿意花很多功夫做好这件事情。他坦言,之所以投入这么多精力,是因为他觉得一本好的教材对于培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教育学》这本教材定义了两个功能,一是打基础,二是引入门。不少学生都跟我说过,郭老师,我是读你们编的《教育学》这本书入门的。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准确。教育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是必须掌握的,只要把基础打牢了,学科根基稳了,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进一步地提高、发展与创新。”老人笃定地说。
“我觉得,一本好的教材、尤其是高校教材绝不是抄抄写写的简单工作,而是一件复杂而有创造性的工作。若教材内容无重大改变,仅在章节的分合及编排顺序上下功夫,那也只能算是新瓶装旧酒,又有多大的价值呢?教材编写是一种科学研究,只有以科研的方法与精神去编写教材才能确保教材质量。”在郭文安看来,教材的编撰不只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更是一个将适合时代和学科发展需要的学术观点与创见融入教材体系的过程,致力于促进学科理论的发展与提升。

教育学院师生在第35个教师节看望郭文安教授
郭文安不仅对《教育学》这本教材编写倾注了大量心血,身为教师的他也非常尽责。“我对学生是比较热情的。有时候他们拿着写好的文章来找我,请我帮着看看,我都会答应,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会全心全意地提出些建议,告诉学生怎么修改。我性格比较温和,学生们还是挺愿意找我的。”当被问及这样是否会比较辛苦时,老人坦然一笑:“当你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而且,跟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教学相长。”

郭文安教授九十华诞(王健 摄)
2021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郭文安获评为该出版社70位功勋作者,肯定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高校课程教材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教育学院也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再度合作,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第八版修订工作,这本发行超800万册的经典著作即将焕发新生。已至耄耋之年的郭文安又开始为《教育学(第八版)》修订而忙碌。“这一次我是主编。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想方设法继续把这件事情认真地做下去。”老人的话质朴又真诚。